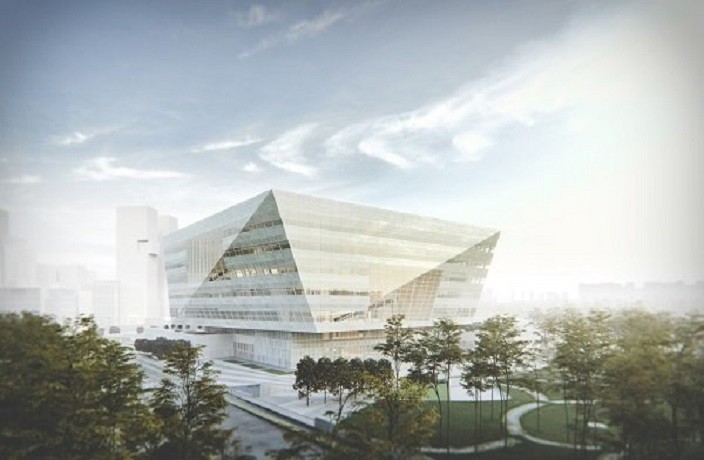文科备受诟病。那么,为什么富人要让他们的孩子学习呢?

根据两位经济学家的一项新分析,对那些认为文科教育不值得投资的人提出了异议。
安得烈·W·梅隆基金会的Catharine B. Hill和Elizabeth Davidson研究了文科教育毕业生能挣多少钱。他们发现,尽管文科专业的工程师没有那么多,但他们的工作业绩可圈可点,文科的价值在批评家那里得到了扭曲。
下面有篇文章,唐纳德·拉泽尔(Donald Lazere)撰写。唐纳德·拉泽尔是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加州理工州立大学英语名誉教授,他提出并回答了以下问题:如果批评家认为文科教育不值钱,那么为什么美国的富裕家庭希望他们的孩子去学文科?
他与安妮·玛丽·沃马克合著了《公民素养之阅读与写作:辩论性修辞评论指南》第三版、他还著有《创作与修辞中的政治素养》、《阿尔伯特·加缪的独特创作》,并且是《美国媒体与大众文化:左派视角》的编辑。
唐纳德·拉泽尔撰文

那些嘲笑文科的人喜欢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有着奇奇怪怪名称的头衔,或者专业度非常狭隘的大学文科课程,如文学或哲学研究,或者教条主义之类的课程,如“认同政治”。
这种论调正确与否,往往备受争议,但它们也可能是正确的,只是正确的程度各异。我同意这种观点:此类课程放弃了文科教育最重要的使命,即社会学家阿尔文·高德纳所称的“批评话语文化”。文科学士的学生、教员和毕业生,不管他们的阶级、种族、性别、身份如何,“批评话语”理应成为他们的共同语言。

如果一个国家想要进步 … …民主应奉献于“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奉献于大众,奉献于每一个人,在每一位公民身上,它应该产生什么样的能力?至少以下几点至关重要:公民有能力思考影响国家的政治问题、能够审查、反思、说理、辩论,不必盲目追随传统,听命权威。以上说法似乎足够明智,但却导致了令人烦恼的两难境地。
首先,为什么这些理念往往来自有诸如玛莎·娜斯鲍姆执教过的“精英”学院,如芝加哥大学或常春藤联盟学校?我们为什么要假定这些理念对那里的精英学生有价值,而不是对全国每一所大学或每一所K-12学校的学生有价值?
事实上,此项政策最先于2010年由全国州长协会(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授权的“州立共同课程标准”提出倡议(尽管尚未广泛实施,且备受争议),主张在K-12中进行全国性的指导,以证明“说服性推理和证据使用”对民主国家的公民职责至关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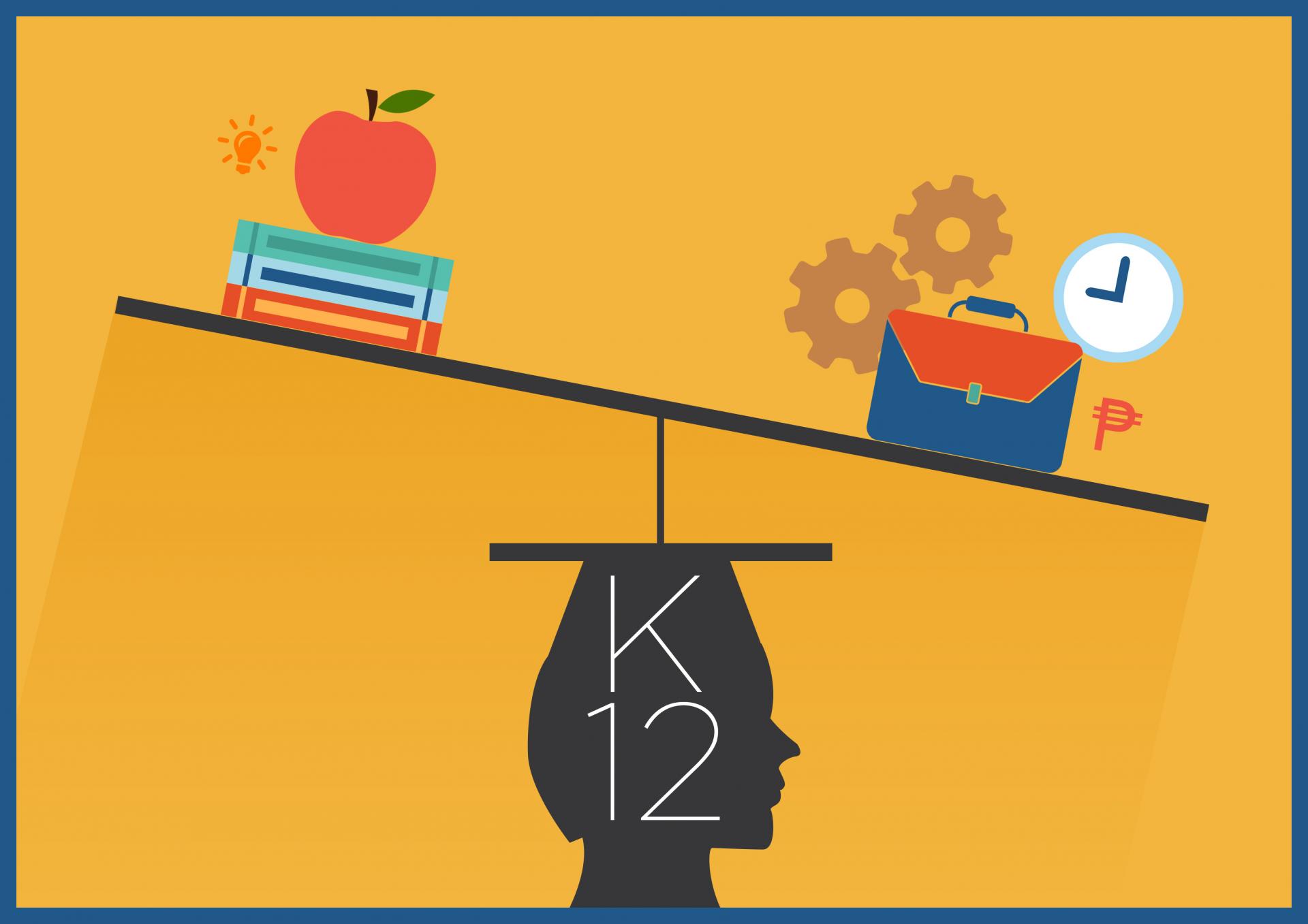
“各个社会阶层都将发现价值和天才,配备完整的教育培养,就可以克服财富及出生门第对社会公信产生的负面印象”。
此外,这种全民教育模式将提升人民大众的道德尊严,维护自身的安全,让政府工作井然有序,并完成使他们有资格选举真正的亚里士多德(或“精英统治”)的伟大目标。这样做,是为了政府的公信,也为了将伪善者(即出生权贵人士)排除在外。
关于教育的内容,杰斐逊在一封如何学习的信中指导侄子彼得·卡尔:“大胆地提出问题吧,即使上帝存在没问题;假如真有上帝,他应该更加赞成理性的尊敬,而不是盲目敬畏。”
把文科教育与富人区分开来的最棘手的矛盾可能是:文科课程中的许多“经典”著作,尤其是人文学科中的著作,如同苏格拉底在雅典教导学生接受贫穷生活,以便寻求智慧和美德一样 – 这种教义极具颠覆性,直接导致了对他的逮捕和处决。
苏格拉底对《新约》做了预示,主题是对财富的谴责 -- 尽管几百年来富人的鼓吹者已将福音合理化,声称富人进入天堂并非那么困难。
随后一些“西方文明”的课程中有一些声名狼藉的白人男性所写的经典著作 -- 无论他们有多么公正地批判性别、种族偏见、不公不义 --绝大多数人仍强烈反对财富和富人,尤其是在工业资本主义兴起后,被冠以“黑暗撒旦的磨坊”的恶名(威廉·布莱克)。

19世纪中叶的美国,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所著的《美国学者》,与同时代的欧洲马克思有相似之处::“最有前途的年轻人... ... 对商业管理的条条框框很反感,其才能受到制约,只能从事苦力活,或者死于反感- 有些人选择自杀。“
爱默生的学生亨利·大卫·梭罗(和爱默生一样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在他的文章《没有原则的生活》中也对此表示赞同:“获取金钱的方式无一例外会让社会恶化”。并且,“没有什么,比不间断的商业更有悖于诗歌、哲学和生活本身了。“
马克吐温在19世纪后期提出了了“镀金时代”一词,他当时写道:“拯救伟大的共和国是不可能的,她很伤心……政府被掌握在富人和他们的衣食父母手中;选举变成了一台机器。没有原则,只有商业主义,没有爱国主义,只有钱袋。”
今天的富人或想致富的人都希望接受精英文科教育,我们能从这种反常现象中得出什么结论呢?要知道这些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对富人的诽谤。
对这个问题最有可能答案,已经与教育史深深地纠缠在了一起。如“绅士教育”的概念对于那些社会地位十分稳固的人来说的确是“绅士教育”,他们不是为了谋生而工作,所以可以无私地思考并写下对自己所属阶级的批判 --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或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的管理模式下,提出政论异议。
还有一个更愤世嫉俗的理论:尽管被文理学院录取,从学院毕业,需要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文理课程的实际主题和学术严谨性,基本上都是常春藤级别文凭的一个初级价值表象,即获取文凭的关键是社交活动,以及与文凭相对应的社会地位,如同设计标签或秘密协议。
还有一些家境殷实的学生,通常称之为“遗产入学”,他们只想做“C分绅士”,很少会花时间在学术上,但频频出入于社交和派对场合。
即便如此,为什么四年或四年以上的“批评话语文化”沉浸式学习,仍然是金融和社会精英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个原因至今是个谜。
几年前,我在位于农耕之乡的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教授了一门GE&B必修的文学入门课程。一个家里拥有一个大牧场的学生不停地激怒我:为什么他要把时间浪费在通识教育上,而不能只学习农业管理课程?
我再三尝试,并希望回顾通识教育的理由,并解释为什么它受到社会运动者和振动者的青睐,包括杰斐逊的道德责任观和努斯鲍姆的“思考影响国家的政治问题,审查、反思、辩论和辩论的能力”。
在我的一次努力之后,他突然说:“你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学这些东西,这样才能在高尔夫球场有谈资吗?”也许他说到了点子上——尽管我不能想象在我知道的任何一家乡村俱乐部里会有关于苏格拉底或梭罗的讨论。
对于这些悖论,其他可能的解释或解决方法都过于复杂,甚至无法猜测。可以这么说,如果学生能接触到政治经济现状,或者有可能成为是政治经济现状的主要受益者,教育能让这些学生对此做出积极评判,那么这个教育体系有完美了,而实际上,我们离这个完美体系还差得很远。
与这些悖论更为相关的实际后果是:K-12和大学的文科教育并没有让“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享受到,它受到了立法消减预算,学费飞涨,学生贷款债务飞涨和政治反智主义的制约,这已然成为国家的耻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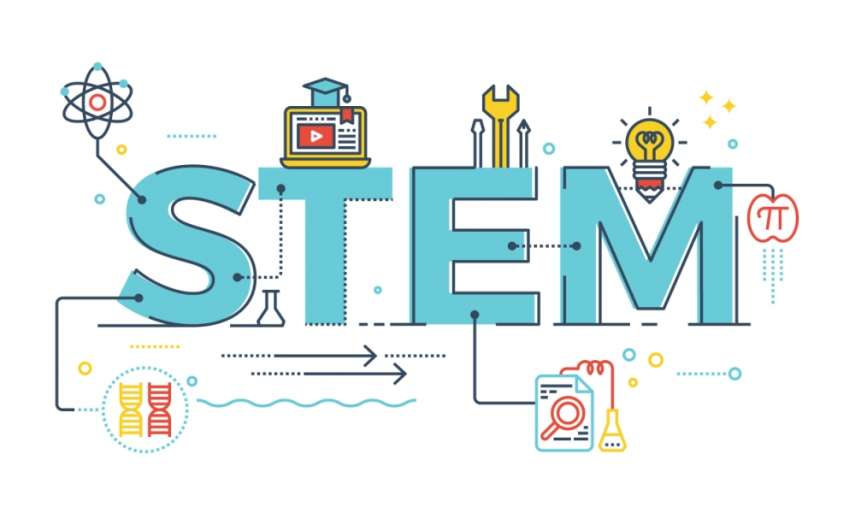
对于一个开明的公民来说,很少听到任何著名的政治领袖对通识教育的辩护——即使是像贝拉克·奥巴马这样的民主党人,他的教育,在总统任期前写的关于文科教育的两本书和演讲比任何一位总统记忆中文科都更加深入人心。但作为总统,他却不得不为STEM教育和学校私有化进行游说。。
我看到了国家放弃通识教育的几个理由。特别是在正统宗教信徒和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群体,他们反对任何“不尊重传统和权威”的教育观念 -- 即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教会和民族主义的权威。
第二,为K-12私有化和加强公司对高等教育的控制而进行的大规模游说,力图将教育转变为一个营利性企业,用公司体制化取代自由学习模式下的教师和学生。主张大规模减税和私有化的游说者格罗弗·诺奎斯特承认,他的政治目标是“在教育和其他公共就业方面,粉碎左派做法“。
此外,在美国社会和政府的几乎每一个分支和阶级上都占上风的富人中,许多人都非常清楚通识教育的价值,因此,因此按照杰斐逊的说法,他们对其子女严加限制,以防止弱势阶层”击败来自财富方面的竞争,并产生社会公信“。
这些保守势力在公共教育领域无情削减预算的借口是为了预算紧缩(当涉及到军事开支、天文数字的个人财富、企业利润和竞选捐款时,这都不是问题),或者确保消除通识派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正确性。这些保守主义者会把普及尚在襁褓中的通识教育连同通识偏见当作洗澡水一起泼出去。

最后,除了富人以外,通识教育及其他事务都面临着危险。长期以来,许多文科院校的毕业生院系的杰出之处,不在于财富,而是他们在纯社会科学、艺术和人文科学等领域,作为学者或实践者、公共事务权威、“公共知识分子”和“说话的头脑”或活动家等方面的卓越地位 – 或者追溯到19世纪的废奴主义、女权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方面的社会正义活动家。
美国的人才资源需要加以保护,以防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所说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的复苏。
如果您还没有关注优智家,请扫描下面的二维码:

[图像来源:百度;封面图像来源:华盛顿日报]